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启动:超前消费、猛加杠杆是通往破产之路
个人破产制度是近两年的新生事物。所谓个人破产重整,是指债务人在面临资产清偿困境时,在法院的主持监督下,制定多数债权人认可的债权调整方案和资产保值措施,并努力实现当下及未来的可持续财产增值,避免资产的完全清算,给予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东山再起”的机会。
目前,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份已有不少城市开始进行个人破产制度的试点工作。据报道,6月20日,我国境内首宗个人破产案的债务人梁某某收到民事裁定,裁定该案已执行完毕,并依法免除了梁某某未清偿的债务,他也因此获得经济“重生”。截至目前,如深圳市中院已收到个人破产申请1635件,已立案审查411件,裁定受理破产申请117件。
通向破产的道路之一:超前消费
在个人破产案件信息网上,我翻阅了多份个人破产申请公告,有人是因为超前消费背负了巨额债务;也有人是看到股市暴涨带来的发财机会,不惜借钱炒股,也因此背了一屁股债;还有人是受疫情、公司裁员等影响,导致失业、经营不善、收入下降,短期内无法偿债。
比如,某运营商职员白先生,刚开始公司福利待遇好,并于2007年年底买了第一套房。2010年,他的女儿出生不久后,原本想用于换房的房款由于投资失败逐渐被消耗,随后,由于女儿年龄小,妻子辞职在家带孩子,房租、孩子教育、生活费逐步增多,他也没有控制自己的消费,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到2014年,由于福利待遇缩减、收入骤降,入不敷出的现象更为严重,他开始用信用卡弥补消费的缺口,利息不断增加。
除了白先生高估了自己的收入稳定性及未来增长空间,低估了孩子出生、妻子辞职、盲目投资等所叠加的资金支出压力外,不加节制的消费带来债务进一步增加。2015、2016年,白先生通过三家银行授信高达89万元,就此,他用卡养卡、以贷养贷,每年超出他收入外的消费有20万元,每年的利息也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通向破产的道路之二:杠杆投资
申请个人破产的庞先生则是另一番情形。从2014年7月到2015年3月,股市行情火爆,他也在此时开始投资股票,30万元现金全部投入股市。在满仓连续跌停后,庞先生想抄底、翻本,于是从银行贷款继续投资,到2017年12月,累计亏损182万元。
然而,庞先生仍未停手,在网友的推荐下,庞先生于2017年9月进入商品期货市场进行投资,前后累计投资140万元(个人积蓄10万元、银行贷款130万元),但是依然未能赚钱,累计亏损138万元。也就是说,庞先生前后在股市、期货市场上共亏损了320万元,其中债务约280万。
而据庞先生申报,他目前的月平均工资为6613元,名下无车无房,现金、银行存款均为0元,第三方支付平台有17.87元,住房公积金内有1.75万元。
按照庞先生的现有收入,如果他要还清所有债务,哪怕不吃不喝,将所有工资全部用于还债,也要至少30多年。
纵观庞先生的欠债过程,抱着在股市、期货市场一夜暴富的幻想,在本金仅为几十万元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借贷达数百万元,属于典型的加杠杆行为。
通向破产的道路之三:不可抗力
除了上述两类情形,另一类个人破产申请人的原因,也许能获得更多理解和同情。个人破产申请人李某从事销售工作,2020年10月购买了一台小汽车用于业务开展,借款期限42个月,月供1883元。当年11月结婚,2021年7月女儿出生,妻子没有工作。因妻子属于高龄孕妇,孕期及产后花费了将近5万元费用。
孩子出生后,李某父母来深圳照顾孩子和妻子,各种费用增加,其中房租水电费3000元,一家五口生活费7000元,孩子奶粉尿片等1500元,社保费2000元。受新冠大流行及防疫影响,李某收入大幅减少,月入仅约6000元。为了填补日常生活所需缺口,靠信用卡和网贷周转资金消费,2年多共负债约30万。
此外,李某投资一笔钱入股了一家公司,但公司尚未盈利,无法收回本金。由于被债权人催收,已经影响李某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李某表示,自己愿意努力工作逐渐偿还全部本金,恳请法院和债权人给一个重生机会。
相比于前两位,李某因工作受外部突发因素(疫情)影响,收入锐减,同时又因结婚生子,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可以说,他的欠债大多可归因为不可抗力所致。随着我国经济回复正常化运转常态,李某工作收入有望恢复到从前甚至更高。而他的妻子也可在一段时间后,再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
如此,李某是具有一定还款能力,其欠债原因也情有可原,也因此,法院受理了其个人破产重整申请。
“一人做事一人当”除非不可抗力
从上述三类案例来看,个人破产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法院需根据不同申请人的情况,及其所反映的信用程度、责任细分及偿债能力等,从而选择受理或不受理申请。
这也说明,个人破产制度面临的挑战及风险不容忽视。当下社会信用体系仍待进一步完善,最高法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14日,全国“公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超800万。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某些老赖瞄上了个人破产制度,将个人破产制度视为新的债务逃避路径,比如将个人已有资金悄悄转移,或者“假离婚”分割及转移财产,或将房产无偿赠与他人等,然后申请破产,如此岂不是让个人破产制度成为老赖滋生的温床?
此外,各类金融衍生服务的推出、金融机构为了完成业绩指标而过度发放各类消费贷、房贷等现象,会造成欠债现象的加剧。央行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22年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98亿张。除此之外,网络上还有众多低门槛授信金融服务,都在向年轻人释放信号:今朝有酒今朝醉。个人破产制度的推行,是否会导致个人借债风气与金融机构房贷门槛的“一高一低”,引发更为严重的全民举债消费风潮?
在传统的民间债务体系中,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债务责任是明确的、单方承担的,而个人破产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将债务责任延期甚至分解。假设真的有人利用这一模式逃避债务,债权人是否有权向“查事不明”的法院、信用验证机构等追究相关责任?
法学家指出,相当数量的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引入自然人破产程序,同时立法差别很大,有些国家的立法强调社会和行政方面,有些国家的立法更重视当事人的权利。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如何更好规避可能带来的风险与责任转嫁,仍需法学界、司法机构等各方不断论证及实践。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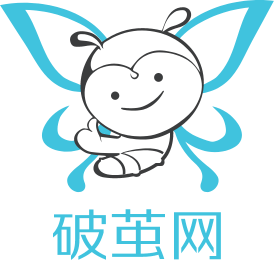
 网站导航
网站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