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龙头国企濒临破产,民企接手重整,纪录片“绝境求生”获大奖
【发布时间:2023-12-04 15:21:50 】 【信息来源:破茧网】
中国民营企业不仅开办《美国工厂》,也帮助中国戈壁工厂“绝境求生”
近期,讲述中国民营企业家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故事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引起了海内外观众的热议。《美国工厂》展现了在中美文化差异背景下员工和管理方的关系;在中国西北,同样有一家工厂面临着职工和管理层之间的沟壑:虽然没有文化差异,却事关国企员工和私企员工的身份认同。
曾是钛白粉行业龙头老大的中核钛白一度走到破产边缘,面临清算退市的风险。民营企业家李建锋的接手,让中核钛白走上破产重整的道路。民企救国企、劳资关系处理、债权债务关系整理……中核钛白的转型之路处处坎坷。
纪录片《绝境求生》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展现出国企“处僵治困”的冰山一角。该片荣获了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最受社会关注纪录片”、国家表彰“2017年度优秀纪录长片”和“优秀摄像”奖等多项大奖。
曾是行业龙头国企濒临破产,企业职工何去何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允许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二十多年来中央不断推行改革措施,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中核钛白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钛白”),曾经的钛白粉行业龙头老大。中核钛白地处甘肃一片戈壁滩深处的核城四〇四,曾经背靠着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是核城人眼中的“金饭碗”。2007年8月,中核钛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甘肃省第一家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
上市两年多后,中核钛白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这个中国钛白粉市场的“黄埔军校”,濒临破产。
中核钛白的第一大股东中国信达多次派工作组前往协调处理此事。经营不下去的企业低效、浪费、腐败,“中核钛白还办过养猪场,为了吃到回扣,就是杀一头猪也要层层批准。”时任信达证券公司副董事长郑成新说。
据了解,面对中核钛白的困局,中国信达请了时年八十岁的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司副司长许美征,来主持中核钛白的重整设计工作。著名的“中国上市公司破产诉讼第一案”郑百文案,许美征就是主要操刀者。
据许美征讲述,原本她以为这是一个卖壳的案子,即把没有价值的资产挪出上市公司,再找人买壳上市。到了甘肃才发现,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卖壳的话把壳里面的资产和员工掏出去就行了,可是那样我们对得起‘核二代’的父辈吗?他们都是当时顶尖的精英、科学家,为了国家来到戈壁滩奉献一辈子。核城周围什么都没有,让他们的子女下岗了到哪里去找工作?”许美征说。
许美征分析,中核钛白作为曾经的行业龙头,又有军工企业的底子,陷入困境的原因不是资产没有价值,而是出资人缺位,管理人以权谋私。“他缺的是一个老板。”最终,许美征敲定一个“顾两头”的方针:既要顾企业重生,也要顾职工保障;引进一个并购方,把中核钛白的资产盘活。
民企接手铁饭碗变“泥饭碗”,职工曾为此集体上访
第一大股东中国信达的股权由债转股而来,根据国家规定,中国信达不能插手中核钛白的经营。中核404厂和中核钛白曾有嫌隙,也不愿插手。郑成新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民营企业,“中国钛白粉行业里大概有70多家企业,我们前后比较了54个备选重组方。”
听说自己的“铁饭碗”要被换成“泥饭碗”,职工们不干了。从国企主人变成给人打工,职工的思想上一时难以接受。“一旦这个企业改制成私企了,将来我们的生活都没有保证了,”中核钛白检修车间职工陈武说。“民营企业一旦进来,很多人就认为失业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保障了。”中核钛白生产部车间副主任高玉峰说。
2009年,民企江苏金浦有意买下中核钛白,引发了中核钛白职工的集体上访事件。纪录片《绝境求生》的开头,就拍下了职工们组织集体上访的场景。厂里的大喇叭播放:“中核钛白这个厂子他们可以去卖,但是中核钛白的职工也可以随他们任意去卖吗?”
郑成新也对引进民企有自己的担忧:“担心他们一走了之。”最终,郑成新选定了无锡老板李建锋。李建锋18岁起就跟着父亲搞钛白粉,从一个乡镇企业起家,到管理家族企业,有20多年的从业经历。李建峰对钛白粉事业有热情,也有过并购国企的成功经验。
经历过几次民企进入又退出的“折腾”,中核钛白的员工对李建锋的到来完全麻木。“不管谁来,都是托管一段时间,捞一笔走人。”有职工议论。
许美征担心长春通钢的悲剧会在中核钛白重演。2009年7月,民企建龙集团参与通钢集团的重组,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建龙集团委派的通钢集团总经理陈国君被工人群殴致死。
中核钛白的机器设备老化严重,李建锋想换掉,有职工警告他:“这些设备都是当时花了大价钱从国外进口,现在即便破烂了也是国有资产,不是你想卖就卖的。”有人故意破坏生产砸烂设备,以为厂子倒了自己就可以回中核工业了,国企员工身份就保住了。还有人将李建锋一纸告状信告到了省里,省政府派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月,最后下了结论:李建锋做的是正常的经营活动。
李建锋认为自己将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做好职工工作上。“我在这儿托管,你以为我是管经营去了?我可没去,我找所有的职工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这些核二代比一般的职工知道的事多得多。”“我就告诉他们,现在车间干净了窗户亮了,不是我给你打扫卫生,是你自己做的;原来车间灰头土脸,也是你自己做的。”
渐渐地有职工接受了中核钛白国企变民企的现实。“我觉得中核钛白转成民企、私企是必然的,这是市场逼迫的,一心想着等靠要是长久不了的。”中核钛白技改管理员王顺民说。
中核集团和中国信达也为稳定员工做了工作。在多方努力下,中核钛白的重整计划顺利推进,摆脱了清算退市的命运。职工人均拿到10万元的安置费,并和李建锋签订了鼓励多劳多得的新合同。李建锋说,中核钛白的员工还是好的,以前只是缺少一个好的机制。
“《美国工厂》中的曹德旺福耀公司摆平美国工人靠的是中国计谋:离间计、以毒攻毒、枪打出头鸟;而《绝境求生》中的精英拯救中核钛白靠的是情怀和责任信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涌评价到。
专家指出应正视破产,破产重整还有待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评价中核钛白案时说到:“现在还不能说成功,只能说顺利。”他认为从破产法角度来看中核钛白并购重组案具备了全要素,是市场化法制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许美征认为我国在破产重整方面的实践还存在很多不足。“现在好多人一说破产,就是破产清算了,这是基于大陆法系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但实际上破产不止有清算,还有重整,破产重整是企业新陈代谢的一个正常的过程。现在这里面有观念问题、有利益问题、有权力问题,是很复杂的。”原国资局企业司司长管维利也认为对破产不能片面认识,“破产不一定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观念不能凝固化”。
许美征介绍到,破产重整是英美法系在20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和我国实行的大陆法系有所不同,中国破产重整的法律还有所滞后。许美征将自己参与过的郑百文案写成研究报告,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新破产法起草小组,一些建议被《破产法》采纳,成功促进了破产重整的适用。
据了解,破产重整和破产重组的概念并不相同,虽然都是指企业在面临重大生存困难时,通过清理债权债务关系,引入战略第三方,通过企业整体转让、易主经营等方式,使企业避免破产清算获得新生;但是,破产重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而破产重整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
破产重组没有法律框架约束,股东、债权人之间都是自愿协商,退出不存在法律成本;破产重整是由法院主导的一种诉讼程序,受到法律框架约束,有法律成本,谈判各方也会因此付出更大的诚意。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 马嘉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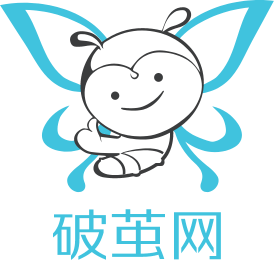
 网站导航
网站导航

